
“麥家”這個名字對于當下的觀眾和讀者來說并不陌生,這既得益于他的小說《暗算》曾獲得中國文學最高獎項——茅盾文學獎,又因為他那些風格獨特的小說頻頻被影視化。《風聲》《追風者》《暗算》等影視劇播出,讓更多人了解到麥家,也了解到他筆下波譎詭異的地下情報工作以及神秘魅惑的天才故事。近期上映的電影《解密》便是這些改編作品中的佳作。導演陳思誠借助新媒介技術,為觀眾呈現了一場視覺體驗上的創新。回歸《解密》原作小說,麥家的敘述則更令人唏噓感慨。電影與小說的互文性,讓我們得以管窺隱沒在歷史背后的無名英雄,一種融于歷史幽暗處的堅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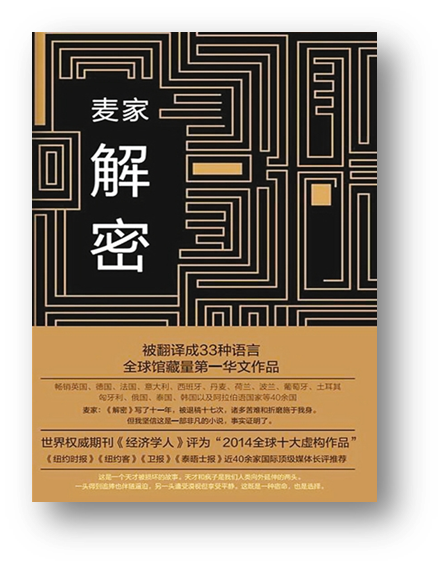
另類的“奇才”少年
在麥家的文學世界中,那些天賦異稟,甚至近乎神秘莫測的奇才們,構成了他筆下的核心人物群像。無論是《解密》中的容金珍,還是《風聲》中的李寧玉,抑或是《暗算》中的阿炳、黃依依,他們都以超凡的才智和獨特的個性躍然紙上。在《解密》中,麥家這樣描繪容金珍出生時的外貌:烏發蓬蓬,頭顱碩大無比。容金珍波瀾起伏的一生在出生時便顯露端倪。隨著故事的展開,容金珍的數學天賦以及對密碼的敏銳洞察力逐漸展露無遺,這構成了容金珍天才的傳奇一生。
但與以往文學作品對天才近乎完美無缺的描述不同,麥家筆下的天才無疑“問題重重”。比如在《解密》中,容金珍性格中有“偏執和激烈的一面”,“如果有什么破了他忍受的極限,或者觸及了他心靈深處的東西,他又似乎很容易失控,一失控就會以一種很激烈、很極端的方式來表達。”類似的“問題天才”在麥家筆下不勝枚舉,《暗算》中的“聽風者”阿炳“既像個孩子,又像個瘋子,既可笑,又可憐,既蠻橫,又脆弱。”這種對天才的另類書寫,是麥家小說獨具一格的地方,亦是麥家小說的文學貢獻所在。回到麥家開始寫作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,彼時的小說界傾向于“消解英雄”,而麥家則“堅信英雄之于文學的魅力”。為此,麥家筆下的“問題天才”便是在“消解英雄”和“重塑英雄”的寫作路徑中開辟的第三種模式。正是因為“問題”的設定,使得麥家筆下的人物在后期的命運轉向中,為讀者提供了更為震撼的心靈沖擊。
從“問題奇才”到“時代英雄”
“解密”是麥家小說的主要題材,小說借此巧妙地將“問題天才”置于時代洪流和家國大義中,從而實現小說的升華。如果只將麥家的小說簡單歸類于以獵奇為主的諜戰故事,無疑是對麥家作品的矮化。在扣人心弦的情節背后,麥家小說的真正魅力在于對人性深刻的洞察,以及對信仰的反襯式書寫。在《解密》中,麥家直接且著重地突出了破譯工作的殘酷性、隱秘性與重要性。他將破譯事業描述為一樁“神秘又陰暗的勾當”,它將眾多人類精英折磨得死去活來。在《解密》的結尾,容金珍也終于因為長期破譯工作而精神崩潰,從天才淪落為精神失常的病人。但這項殘酷又重要的工作,卻始終被隱沒在黑暗之處。自從容金珍參加破譯工作之后,“沒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,他隨著吉普車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,有如是被一只大鳥帶走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,消失了。”隱沒在歷史深處,既是解密人的悲哀,亦是他們不為人知的榮光。
縱觀全書,直接闡述理想、信仰的表達幾近寥寥,但在這樣的留白中,我們讀到的是一個時代的精英群體被家國情懷所包裹的眾志成城。當金珍第一次準備走出家門時,養父小黎黎告誡他:屋里是你的家,屋外是你的國,無國乃無家。小黎黎以此作為激勵金珍入職701的決心。在全書的結尾,金珍的妻子小翟在提到是否后悔與金珍的婚姻時,“小翟像突然驚醒似的,睜大眼,瞪著我,激動地說:‘后悔?我愛的是一個國家,你能說后悔嗎?不!永遠不!’”全書避開了對主人公容金珍家國大義的直接書寫,卻借助幾個配角支撐起了金珍從事破譯工作的核心動機,即家與國的嵌套,是個人命運與民族大義的深度融合。走出家門轉而投向破譯工作的金珍,在此實現了從“問題奇才”向“時代英雄”的華麗轉變。這不僅是他個人成長的里程碑,更是對那個特殊時代背景下,無數默默奉獻、為國擔當的英雄們的生動寫照。
隱沒在歷史暗處的堅守!
縱觀容金珍的一生,他似乎在不斷失去中延伸。他一出生就伴隨著母親的離世,由此注定了他終生飄零的命運。在隨后的歲月里,他不斷地與親人告別,與恩師“反目”,與社會斷聯,最終連他那天賦異稟的才智和理智也離他而去,他變成了一個沉溺于自言自語的瘋子。但與此同時,金珍的一生也是不斷獲得的一生。他得到了洋先生和小黎黎家庭的庇護,得到了師母的溫暖。遇到希伊斯后,這位伯樂進一步挖掘了金珍的數學天賦,為他走向解密工作,繼而破譯紫密走向人生的高光時刻奠定了基礎。不僅如此,在歷史的長河中,容金珍的名字將會被永遠銘記,他的傳奇故事也將被賦予更多的榮耀與敬意。
事實上,不止容金珍,在《解密》中,身份始終撲朔迷離的鄭局長、自嘲平庸的嚴實、默默付出的小翟,他們其實是另一個“容金珍”,我們的國家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一個又一個的“容金珍”,才有了今日的成就。在榮獲茅盾文學獎之后,麥家鄭重其事地對曾經的戰友表示感謝:“我知道,時代變了,但我相信他們沒有變。他們不會變。他們不能變。他們依然是從前,依然是無名無利,卻無私無畏,這是一個消解英雄和崇高的年代,同時我們又無比需要他們。”
文/董小玉、盧松巖



600bd524-6a81-498b-8e10-6aff1cc18895.jpe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