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《生活藝術》出版于2024年,是英國學者齊格蒙特·鮑曼在現代性思考的延伸中完成的著作。英國當代社會學家安東尼·吉登斯對其評價到:“他用非凡的才華和創造力,提出了一個所有人都必須認真對待的立場。”鮑曼作為當代世界最著名的社會家與哲學家之一,總是鞭辟入里地分析現代社會的典型癥狀,集批判性與建設性于一體,為社會科學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在鮑曼的一生中,出版了眾多膾炙人口的學術著作,如《流動的現代性》《懷舊的烏托邦》《現代性與大屠殺》等,體現出了其卓越的社會洞見與犀利的現狀思考。而在《生活藝術》這部著作中,他又以他敏銳的觀察為我們理解現代社會提供了新的視角,而且還進一步給讀者提出了高屋建瓴的實踐路徑,協助讀者探尋如何做一個真正的“人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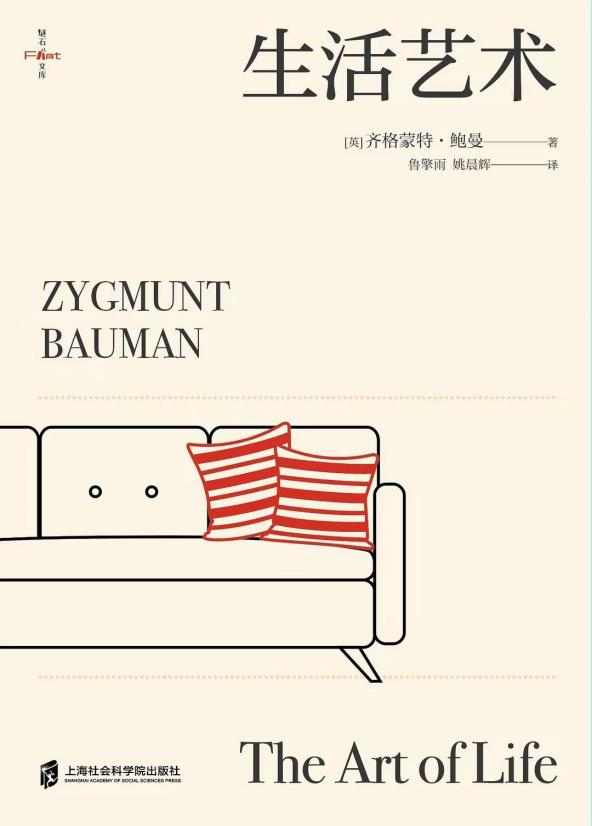
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
《生活藝術》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,依舊建立在鮑曼對“流動現代性”的判斷上。20世紀90年代,鮑曼就提出了“流動的現代性”這一概念,借此來描述當下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。在這個世界中,個人是原子化的,一切都沒有規律可循,也沒有任何可預測的參考框架,世界如液體一樣不斷變化,正是這種“流動性”使人們日益缺乏安全感。在此基礎上,鮑曼在本書中進一步指出:“由于我們盲目崇拜即時滿足,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然喪失了等待的能力。”鮑曼的這一判斷對當下具有極強的警醒意義。縱觀當下的文化產品,微短劇、爽劇等“快餐化”文藝作品風靡一時。相對于強調厚重典雅的文化作品而言,這種速朽產物的興盛一定程度上是人們崇拜即時滿足的表現。在鮑曼看來,這種對即時性的渴求,與經濟市場對文化的染指息息相關。對于文化工業生產者而言,只有創造出即時消費、快速流動的文化產品,才能夠不斷從生產中獲利。因此,資本的產物勢必不能經久耐用,由資本所推動的商品流動,造成并加劇了現代社會的流動性。
偽主體性:流動性社會中的典型癥候
在鮑曼看來,過去,出身決定了人的社會身份。但在現代早期,人們承擔起了建構自己身份的任務和責任。如今,身份認同成為一個極端重要、令人欲罷不能的活動,身份不再具有一成不變的特性,也不再留下牢固堅實、不可摧毀的印記。在當今,人們期望并偏好可以輕易消解的身份,以便再以其他方式將其熔鑄。在過去,身份會延續一生,但現在它只是當下的屬性。
關于身份流動性,鮑曼的論述暗含兩層意思:一方面,現代社會中身份的流動,打破了原本僵化的社會格局,使得人人都可以憑借自身的努力實現階層躍升,從而給予人們生活的期待與希望。但另一方面,隨著資本力量的介入,這種身份的流動被賦予了偽主體性的色彩。此時,身份的流動不再成為人們積極向上的動力,反而異化成為一種阻礙人們找到真實自我的障壁。比如,在五光十色的廣告中,身著時尚潮牌的明星被設定為成功人士的標志,廣告商以此來喚起人們購買的沖動。但只要停止購買,這種時尚的感覺就會立刻消失殆盡。為了維持這種身份,消費者只有通過不斷地購買來裝點自己。
在這個過程中,消費活動占據了思考的空間,消費主體掩蓋住了我們所追尋的真實主體。這其實也揭示出了身份流動性的另一個側面,即不穩定性。這也是為何部分青年即使生活在一個物質高度發達的當下,但仍感到焦慮的原因所在。他們以消費來維持身份的穩定性,這個設定從一開始就是虛浮的,并非他們內心真實所追求的那個自我。因此,這種消費活動沒有盡頭且意義淺薄,并不會留給人們更多值得回味的東西。這是鮑曼給現代人敲響的一記警鐘,亦是他試圖在本書中著重揭示和回應的問題。
如何踐行生活的藝術?
成為獨特的自己是鮑曼生活藝術的核心原則,他引用小說家、生活哲學家馬克思·弗里施在日記里的感想來闡釋他的生活藝術理念。弗里施指出,成為你自己的藝術可以說是所有藝術種類中要求最高的一種。它意味著堅決拒絕和排斥他人強加或暗示自己的身份,逃出海德格爾筆下“常人”所施加的使人失能的控制。簡而言之,成為自己心中堅守的形象,而不是被迫變成外界壓力塑造的模樣。
如何成為獨特的自己?在我們看來,鮑曼從“創造”和“關系”兩個方面做出了回應,前者是成為獨特自己的實踐原則,后者是成為獨特自己的社會條件。就前者而言,鮑曼認為,創造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需要在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中不斷反思與更新。這種創造的思想,與馬克思的實踐原則有異曲同工之妙,都強調在行動中淬煉自我,而不是被虛浮的表面所誘惑蒙蔽。如果說實踐原則強調的是向前邁進的勇氣,那么,創造則需要人們付出更多的主觀能動性,不僅向前邁進,還要求有所精進,有所創造。
就創造而言,鮑曼借助對流動化個體主義的批判來展開闡釋。在他看來,身處高度流動化的現代社會,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呈現出“下錨”和“起錨”的特征,彼此的聯結輕易且速朽,難以建立起緊密有效的社會關系。這里需注意,鮑曼所認為的社會關系并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,而是復雜的、不穩定的產物,它產生于個體對自我創造自由和個人安全感的強烈渴望。所以,在流動化的社會中,鮑曼認為,社會關系的建立須以持久的、緊密的、真誠的互動原則為前提,并以此來對抗流動社會中的速朽關系,從而在人與人的關系鏡像中找到照見自己、發現自己,從而成為自己的那個真實“錨點”。
文/董小玉 盧松巖



600bd524-6a81-498b-8e10-6aff1cc18895.jpeg)
